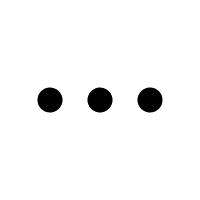罗桂兰,被埋13天后获救
“忆苦思甜”式的思想教育运动持续塑造公众追忆,使记忆在代际中传承。但四十年间,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民间地震记忆的内容开始从歌颂抗震过渡到理性的反思,多元地震记忆的兴起,冲破了官方“一元化”的思想禁锢。“忆苦思甜”是近代革命发生以来,党用以统一群众思想的政治教育方式。在革命思维延续中,官方依然使用这种方式规训民众的政治认同。1977年,唐山地方报纸《唐山劳动日报》复刊后开始对灾区恢复进行持续报道。与专业记者的写作不同,报中还出现了群众来稿选登。作者的身份有地震孤儿、震后重组家庭成员、民警等,都是极为普通的灾区市民。他们通过回忆性文章,来描述他们心目中的唐山大地震。此后,报纸又出现地震“十周年、“二十周年”、“三十周年” 征文的系列专栏。可以说,这些文章深刻的反映了公众的唐山大地震记忆形态。纵观这些文章,绝大部分是以“拯救”、 “重生” 、“辉煌成就”为主题,以革命阶级话语展开叙述,与旧社会进行比较,歌颂新时代的美好。地震二十周年时,那些从未经历地震的小学生们,开始以“听爸爸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形式重温唐山大地震,以此完成“忆苦思甜”记忆的代际传承。当前,这种记忆依然是公众集体记忆的主流。
虽然这种自我讲述式的思想运动深深的影响了唐山大地震记忆的内容,使公众产生了千篇一律、高度统一的记忆,但并不意味曾经经历灾害的人就此停止了对灾害本身的反思与回想。当文革结束走向改革开放,思想不断解放,一些人文社会学领域的知识分子率先突破了思想上“一元”价值体系,开始多维度观察唐山大地震。1980年代,以钱钢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的发表为标志,富有地域特色的唐山大地震文学作品如井喷般层出不穷。同时,一些亲历地震的唐山籍研究者已经开始利用访谈、社会调查、文献法等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审视唐山大地震后出现的各类社会问题,中国地震社会学由此诞生与发展。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唐山大地震成为电影、电视剧的题材。与冯小刚执导的电影《唐山大地震》相比,另一部是由被称为“中国独立地下导演”的王利波拍摄的记录片《掩埋》(Buried)以真实讲述唐山大地震预报失败细节为主,更为注重对灾害事件本身进行深度挖掘。
钱钢
不同的地震记忆也一直在灾区民众中酝酿和发酵,但在一种树立代表性,强调思想规范性的制度下,他们日日的思念与怀想注定无处安放,难以发声。他们只能在寒食节、“鬼节”、地震日等特定时间,以焚纸拜祭的民间祭奠形式抒发应有的悲情。因此,每每此时,唐山的大小十字路口总是泛起火光点点。年复一年,这种来自不同家庭约定成俗的自发性行为逐渐演变为唐山社会中的公祭日,间接推动了政府正式设立纪念日。1992年,唐山民众中又出现了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死难者具体姓名的自发性行动。与官方抗震纪念碑不同,死难者不再以整体的形象出现,而是要被解放回归真实的个体。在公众与地方政府的长期博弈中,2008年唐山最终建立起刻有死难者姓名的纪念墙,并成为大地震主要公祭空间,抗震纪念碑与纪念广场则逐渐失去原有的纪念功用。
在公众不断追寻和还原震灾事件本身的过程里,只要稍稍创造一个自由的机会便会看到,潜藏在国民国家集体记忆表层之下的公众震灾记忆是如此的不同与鲜活。
伴随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方志编纂,唐山大地震记忆正式走入历史。但因地震资料利用等问题,其内容对震灾中出现各类问题缺乏应有关照,灾难中获得的经验教训总结更可谓善乏可陈。一种以反思生命为本的灾害文化建设尚需时日。1985年,唐山始修新市志,时经14年,五卷本,方告完成。其中专设《唐山大地震》、《重建唐山》两章用以记述地震。内容而言,涉及地震地质特点、发震构造、地震历史、前兆现象等,并在震灾纪实的部分中详细的写明了人员伤亡状况和经济损失情况。同时,还附有由地震亲历者讲述编纂而成的“震征实录”。但该部分收录的内容仅局限为描述地震来临时的情景,而缺乏对震前、震后生活变化以及震后救援过程的个人体验回忆。而新编纂的《唐山文史资料》中,除收录了唐山和丰南的抗震纪念碑碑文外,也有亲历者口述。但讲述者的身份都极为特殊,仅仅是当年抗震救灾指挥中心的各级领导与各类英雄、典型人物代表,因而他们的地震回忆内容仍带有较浓的政治宣传色彩。两种地方志中的地震历史编写再次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灾区人民难以忘记党的恩情的两大特定主旨。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在于公众个体仍然难以大规模掌握地震相关资料,进而引发社会对地震灾害的讨论与思考。
目前,唐山大地震记忆及历史,缺乏防灾教训的内容,以生命为代价换来的经验难以转化为有效的防灾力,更没有通过日常学校教育深化人心,为社会提供借鉴并为应对下一次灾害进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