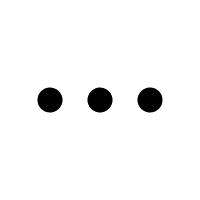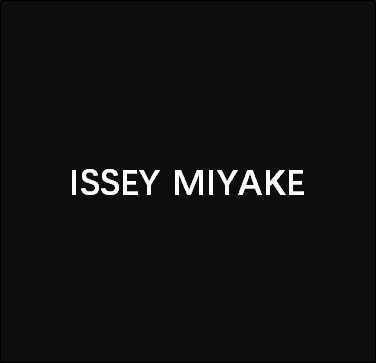灾后恢复:“发展主义下”的城市
巨灾之后,如何应对,才能促使受灾地区尽快实现稳定,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实现复兴发展,是政府与社会所面临的艰巨考验。灾害对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双向双效的作用关系。灾害在造成巨大社会破坏,给人类带来危难的同时,也赋予了社会一种重构的契机,可以籍此改善社会系统内部的结构关系,实现结构转换,使之更加合理化与效率化运行;反之,灾害便会在恢复与复兴进程中继续延伸,进一步形成“复兴灾害”(Reconstruction Disaster)。因此,震后恢复计划的制定和路线导向会对灾后社会给予深远的影响。但自中国走上近代化道路以来,以城市开发为特征的“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思想始终占据重要地位。按照日本学者末广昭的定义,这种思想是以工业化的推进为发展目标,不以个人、家庭、地域社会的利益为最优先,而是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置首位,在这样的前提下集中调动物力和人力资源进行集中管理的思想和管理体系。
首先,不可否认“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救灾促使唐山实现了灾后迅速恢复。地震后,唐山人民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有效的自救与互救,极大减少了伤亡。解救的被埋压人员达到总受灾人数的86%,即约有45万人是通过自救互救而脱险,从而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而这得益于唐山市委依靠残破的社会组织关系网络建立的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它的迅速建立,给灾民以信心,维护了社会稳定,还激发了基层中各种自救组织的出现。国家也迅速做出反应,成立了中央抗震救灾指挥部,决心动员一切力量进行抗震救灾。党、政、军的一些主要负责人担当指挥部成员。地震后,国家共投入110000余名解放军参与救灾;全国各兄弟省、市、自治区对灾区一切所需物资大力支援;派出近20000名医务工作者;工业、交通、铁路、邮电等各方面的行业对口支援共30000多人。
整个救灾工作分为四个阶段,先全力挽救被埋压群众的生命,轻伤就地医治,重伤向外地转运,以及抢运救灾物资;第二阶段,整理和掩埋尸体,安排灾后群众生活,恢复与建立各级组织关系;第三阶段,抢救埋压的重要生活物资;第四阶段,继续帮助群众恢复生产,复建学校、商店、医院等公共设施,组织群众农耕。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恢复,唐山城市基本生活趋于稳定。救助过程中,舍己为人的大情大爱铸就了灾民与援救者之间的深深情谊。
唐山丰南的地裂
发展主义贯穿唐山漫长的灾后修复期。“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一方面创造了唐山工农业恢复与腾飞的辉煌业绩。但另一方面,与改革开放契机相迎合,新一轮高歌猛进的工业城市化进程更注重发展指标,对个体“人”的恢复与发展,关注相对薄弱。这为唐山新生生态体系注入了新的问题,形成社会复兴中的顽疾与隐痛,构成现代“城市病”的病灶。
震后不久,我国结束了十年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开始从原来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在“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学大庆,赶开滦”,誓要“夺取抗震救灾斗争的更伟大胜利”的口号声中,作为全国重要重工业基地的唐山,肩负着比震前更重要的工业生产任务,也迎来了灾后前所未有的大发展。震后的社会恢复完全融入到经济发展的滚滚浪潮之中。虽然震后初期,政府为灾区恢复所制定的各项方针同时兼顾灾民生活安置、城市基础设施恢复以及工业经济和农业生产等问题,但在后来对灾区恢复进程的评价中,却出现了仅以经济恢复指标为判断依据的片面性。不仅如此,在此后更为漫长的灾后重建及恢复期中,国家行政政策却开始更加侧重优先发展生产,并以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为唐山划定灾后恢复的各个阶段。
唐山在经历了所谓“十年恢复、十年振兴、十年发展、十年腾飞”的发展后,变为一个人口接近千万的中国重要城市,创造了令世界惊叹的灾后恢复“奇迹”。在这个进程中,地震的痕迹基本消除,出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生产景象:“耸立的井架天轮飞转,高大的洗煤楼里机器轰鸣,满载着煤炭的列车开往祖国四面八方;井下,电钻欢腾,水枪怒吼,滔滔煤浪倾斜而下”。 这段描写不仅是对唐山灾后工业恢复发展的大力讴歌,更是描绘自然被再次“征服”的挽歌。发展的道路上,唐山地区的生态利益被再次牺牲。
华裔美国学者Beatrice Chen还指出了唐山灾后恢复中的另一个深刻问题,她认为,仅用城市完全再建作为标准横量唐山的恢复力未免太过简单,不可忽视的是后灾害时期的城市化是在强大的政治力的推动牵引下完成的,受灾者的精神外伤与损失的个人影响则被忽视。
作为受灾主体的灾民,无论是人口数量,还是婚姻家庭,乃至灾民心理都需要一个更为长久的周期才能从灾害打击的状态中缓慢复原,因此更加需要整个社会持续的关注。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大行其道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对灾区人口恢复起着强大的调节作用。它改变了长久以来,中国社会灾后人口高调反弹的作用机制,使人口增长被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即便如此,马尔萨斯揭示的灾后人口补偿机制仍然以其顽强的力量发挥作用。震后一段时期,在不影响计划生育大前提下,国家对地震重组家庭夫妇的生育给予了政策上的特别调整,从而出现了一些“团结孩”、“地震孩”。但灾区人口的快速恢复,却并非依靠灾民自体的生育恢复,而是通过政策性的快速人口迁移补偿得以实现。不仅如此,由于地震大量的人口伤亡损失,影响了灾区家庭形态。丧偶、孤儿、孤老、重组家庭、残疾人家庭等纷纷出现。震后,政府为解决数千名孤儿与孤老的抚育和赡养问题,依靠行政力量建立了277所敬老院与育红院,对这些人员进行妥善安置,进行了一场“生养死葬都有指靠”的灾后大善后。然而,从近年来针对地震孤儿的心理调查研究结果来看,无形的精神外伤正在影响他们正常的生活,左右了他们的婚恋观、人生观,他们中的某些个体出现了自卑、焦躁、敌对、依赖等种种变异心理。唐山康复村的残疾人群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心理反应,有人表现出抑郁、失眠、焦虑、自暴自弃等不良情绪。
中国地震社会学的开创者王子平先生,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提出地震对灾民心理伤害的问题。他认为救灾工作中应该包括心理救助的内容,进行“精神救灾”以清除地震给人造成的心理“废墟”,取得救灾工作的全面胜利。这一对灾害的新认识也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出现的。正在经历中国深刻变革的后震灾时代的灾民们,不仅背负着地震给身体留下的伤痛,还要在各种社会关系的打破与重建中找寻自我,不断进行精神与心理上的调试。中国的改革之路既为他们带来了多元化的救护途径,为实现更好的灾后恢复提供保障;但同时,激烈的社会变化也让他们在时代的发展洪流中怅然迷失。因此,如何实现灾民的精神复兴,是新时代灾害应对中的重要课题。
大地震如何被“记忆”?
学者王晓葵曾通过一系列文章讨论过唐山大地震记忆的空间建构,论及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死难者纪念仪式建立“记忆之场”,唤醒地震记忆,并在与受灾地、个人三者构成的复杂关系中影响震灾记忆的塑造。他还提出了记忆社会构图模式,试图证明这种记忆构图的连续性。的确,“记忆”不仅是一个与空间相关的概念,更在时间的演进中制造和产生。尽管王晓葵看到了唐山大地震的记忆框架可以从清代的灾害应对体制中寻找到相似的投射,看到一种貌似的历史连续性,却忽略了隐匿于深处的非延续性。这是由中国的近代化转型所引发的深层历史变革所导致。因此,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与变迁将更丰富的折射出历史时代精神转变的特质。
唐山大地震后初期的记忆塑造,是革命思维的再延续。进入20世纪,“革命”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成立,社会几历雨动荡,但革命思维经久不散。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革时期,整个中国更是进入了“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突出政治时代。在这样的政治意识构建下,一套适用于当下的革命式灾害解释话语体系随之出现,并在唐山大地震的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抢险救灾被视作一场“特殊的战斗”,灾民化身为“阶级兄弟”,军队救灾和全国支援活动则体现了“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并且,抗震救灾的首要目的是一切要为革命工作和工业生产而服务。
具体行动中,采取树立先进集体、先进典型,以及讴歌英雄事迹的方式,达到进一步统一思想以维护政治斗争正确性的目的,并成为震后宣传工作中的重点。经过一元化思想的整合,这些认识转化为唐山大地震记忆的主体部分,从而使灾害本身的记忆与惨痛教训被替代。同样的思维还贯穿于国家一系列地震纪念场所的建立及纪念活动的设立之中。在国家革命意识主导下,官方组织的地震纪念活动不仅一直保留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语境,还在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目标下不断赋予地震纪念以实现“工业现代化”目标的精神动力等新的解释内涵。因此,地震记忆始终与地震事件本身产生着疏离。在时间的沉淀中,唐山大地震的记忆逐渐变化为抗震记忆。而那些真正可以唤醒人们地震记忆的遗迹,损毁现象十分严重。面对难以辨识模样的地震遗址,人们很难置身其中产生回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们与地震灾害之间的情感隔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