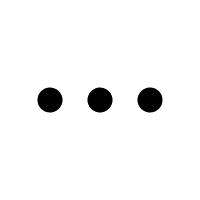“野”得够不够见仁见智
重庆青年报:您曾在采访中谈到剧和小说保持了精神内核上的一致,仍然表现了“人性的张扬、强悍的生命力和狂野的精神”。您主要从哪几个人物上表现这个人性张扬与解放呢?
赵冬苓:人性解放只是一方面,我们和原作不一样。比如原小说里对时代背景的交代是比较模糊的,到我们这儿是比较清楚的,我们把社会环境等都丰富了,我们认为这是比较有家国情怀的一个剧。
第一,我们把这个故事落地了,让它充满了“烟火气”,第二,是我们提出了家国情怀,上世纪30年代一开始什么样,后来又团结起来抵御外敌。
我觉得每个人物都有余占鳌和九儿的人性解放主题。莫言先生写这个小说,两人是彻底反叛的、反对旧传统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起码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但我们是电视剧,是实打实地在讲更丰富的故事。
重庆青年报:在文学和电影里,先是爱情、后是民族仇恨让人物的人性解放,原动力是一条线,而电视剧复杂的人物关系和社会环境让人性解放的动力变成了网。这种变化是否会削弱人性解放这个主题?
赵冬苓:我不觉得。电影和原小说只截取了他们生命中的一段,我们电视剧把他们整个成长变化的过程给它踏踏实实的写出来了。比如余占鳌,他前期是个纯良的轿夫,可能不是原小说那么火爆、那么叛逆,但他一旦走向了叛逆之后,是非常叛逆的。
我个人觉得不削弱,但观众可以见仁见智。有的观众觉得他们“野”得还不够、原作里的狂野精神哪儿去了?也有的觉得他们已经过了。我特别有娱乐心态,有些评论对我有启发,有些我不放在心里。原来电影刚出来也是骂声一片,说它宣扬中国的落后、丑陋,莫言的小说刚出来也被骂过“卖国”,我觉得一个作品说好说坏都正常。
抗日令人性觉醒仍值得写
重庆青年报:前两年,“抗日雷剧”网上口碑一直不好。您写过好几部抗日时期的作品,您觉得抗战时期还值得写、还能写出新意来吗?
赵冬苓:这部剧我们就想写出点新意,包括我们尽可能地不去妖魔化日本人,但今天郑晓龙导演还在跟我聊,审查时有一些东西有改动。
我给重庆写的《母亲,母亲》、《雾都》都没有像抗日雷剧那样,在我眼里,抗战是非常残酷的,五个中国军人不一定能打得过一个日本鬼子,抗战就是以血肉之躯去与人家的坦克大炮拼,非常惨烈。起码在我这,没有抗日雷剧一说的。包括《红高粱》后面写抗战时期,我们写得也是非常严肃的。
重庆青年报:抗日这段时期有什么特殊性、特殊的故事发生生态,吸引您还在这里探索新的东西?
赵冬苓:抗日时期是一个民族灾难时期,原本军阀混战、土匪横行,但有了外敌以后,这些人都团结一致去抵御外侮。
我觉得在抗战以前,中国的民众没什么家国的概念,过去信息也不灵通,对于他们来说,只有这个皇帝、那个皇帝,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有日本人来了,侵略这个国家,你不反抗就要亡国了。
我写《中国地》对这个感触特别深,实际上是外族的入侵使中国的农民有了家国的概念,《中国地》里面的赵老嘎一开始就是你不针对我我也不针对你,后来慢慢意识到国家的概念。
所以抗日的东西不是不能写,是非常值得写,但要看你怎么写,你不能用娱乐化的方式去写。
重庆青年报:《红高粱》里边的人物的觉醒是因为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变化影响与压迫,以及外敌入侵。
赵冬苓:是,到抗战那段你就会看到,余占鳌和朱豪三这两个死敌为什么能最后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到了没办法的地步。
重庆青年报:那么放在当代,当代人身份是否面临压力,需要觉醒?
赵冬苓:这没法回答,我只能说,现在年轻人,受找工作、买房等各种现实问题影响,个性被压抑,希望年轻人能有《红高粱》里面的人的活法。
文/重庆青年报记者席郁兰图片由山东卫视提供